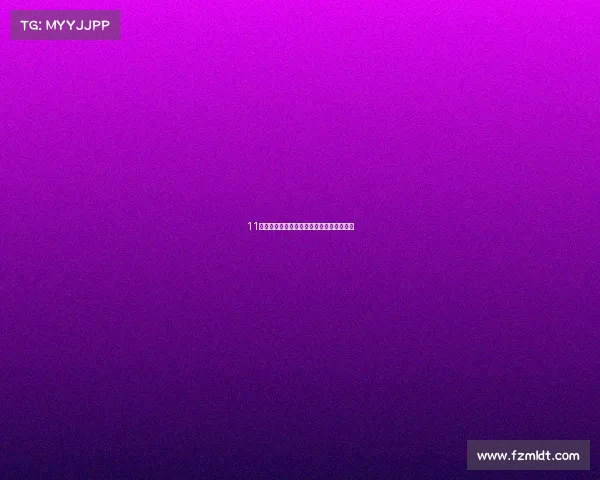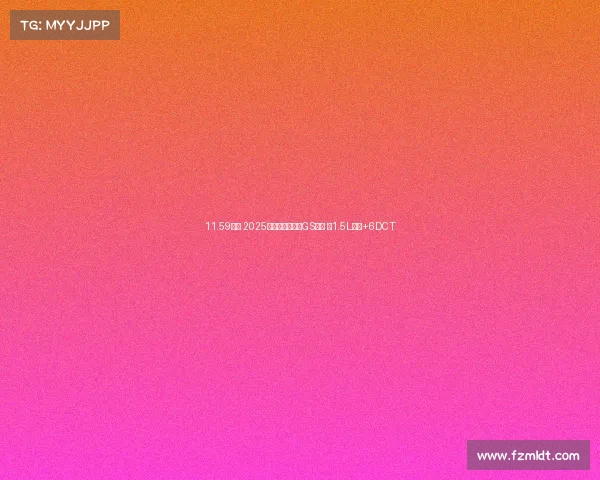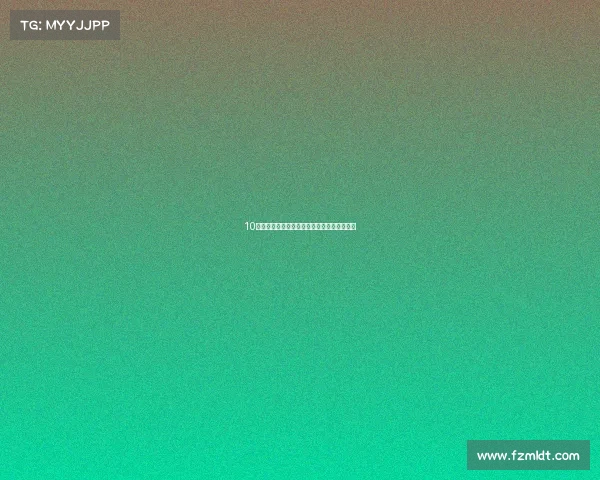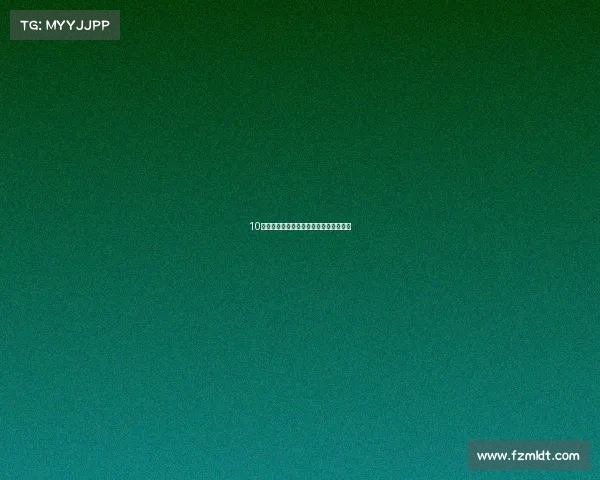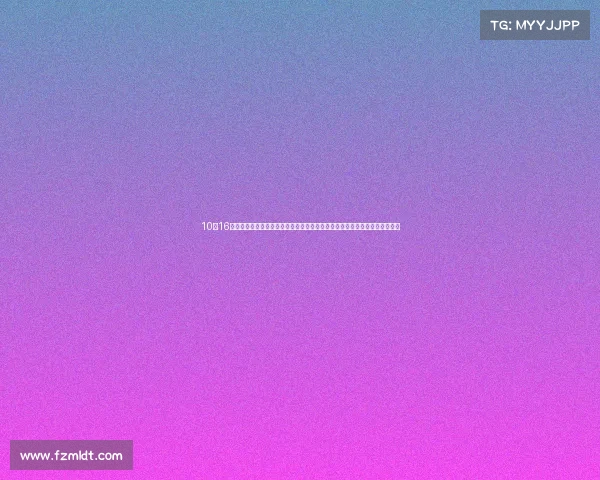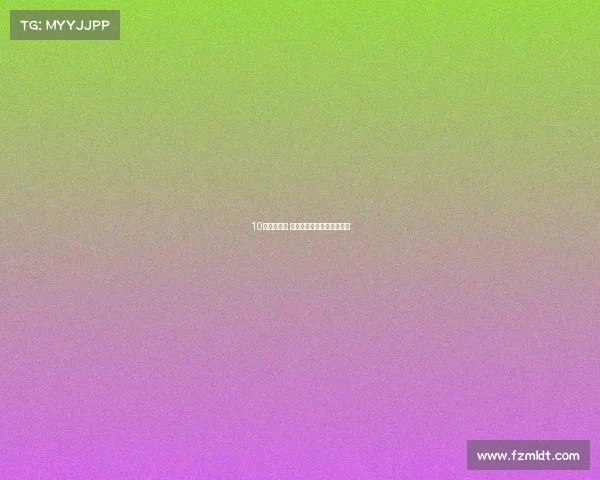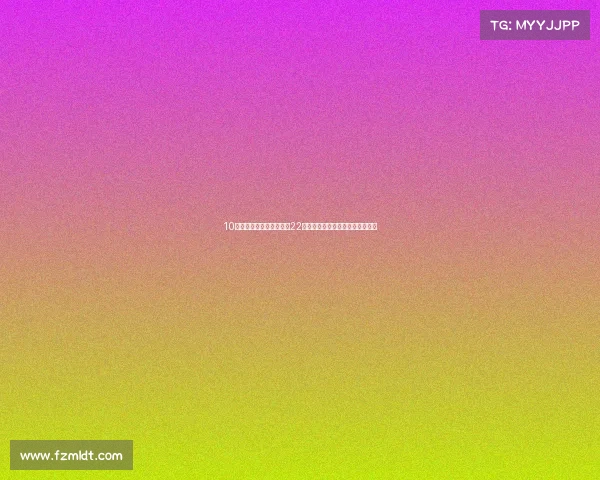旧棉袄里的秘密
"妈,我回来了,只带回姑姑的旧棉袄。"话音刚落,母亲眼中的失望刺痛了我的心,却不知这棉袄里藏着一个我羞于面对的秘密。
冬天的东北,寒风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,像是在埋怨这个世界的不公。
那是一九九零年的寒冬,计划经济的末期,国营企业开始走下坡路,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
我们家住在东北小城齐市一处老旧的筒子楼里,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挤着我们一家三口。
屋里的炉子烧着煤球,散发出硫磺的气味,却是我们抵御严寒的唯一武器。
父亲张长河在齐钢当工人,每天和钢花打交道,那双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盔甲。
母亲李巧云在齐市丝绸厂做缝纫工,她能把一块布料变成漂亮的衣裳,可家里人的衣服却总是打着补丁。
我张小满,市一中的高二学生,怀揣着一个在那个年代略显奢侈的梦想——考大学。
那时候,大家还习惯叫它"高等学府",能上大学的人在街坊四邻都是"文化人",家里祖上都会被传为有"读书种"。
我的成绩在班上算拔尖,老师说我有希望考上省重点,这让父母眼里有了光。
可就在交下学期学费的前一周,祸不单行。
父亲在车间操作时,一块飞来的钢渣溅进了眼睛,紧急送医后虽然保住了眼睛,却不得不住院治疗。
那几天,医院的走廊上总能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影,她在白色的墙边显得格外单薄。
我们家仅有的三百多元积蓄,转眼就花在了手术费和药费上。
家里的米缸见了底,锅里煮的是白菜和土豆,可更令人揪心的是两百元的学费迫在眉睫。
"再耽误交学费,班主任又要家访了。"我忧心忡忡地对母亲说,上学期因为交学费晚了,班主任曾经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家里了解情况,那次我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。
母亲坐在炉子边缝补父亲的工作服,针线在她手里飞快地穿梭,听了我的话,她的手停顿了一下,然后继续缝着,仿佛什么也没听见。
那天晚上,我偷偷起夜,看到母亲坐在昏黄的电灯下,翻箱倒柜地找东西,那专注的背影像极了一个即将赴考的学生。

"咳咳。"我假装咳嗽,母亲慌忙合上柜子,转过身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"小满啊,睡不着?"她问,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疲惫。
"妈,我们家是不是没钱了?"我直截了当地问。
母亲沉默了片刻,叹了口气:"家里是有点紧张,但日子总要过下去。"
我知道,这是母亲式的委婉表达,意思是:确实没钱了。
第二天早晨,刚刚天亮,我就被母亲的说话声惊醒。
"要不,去你姑姑家借点?"母亲小声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。
父亲沉默许久,我透过房间的隔断布,看到他闭着眼睛,脸上的表情比受伤时还要痛苦。
"去吧,但别说我住院的事。"最终,父亲艰难地同意了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,仿佛这句话抽走了他全部的力气。
钢铁厂的工人,那是多硬的汉子啊,可在生活面前,也不得不弯下腰来。
我知道父亲多要强,在厂里从来是别人有困难他帮忙,何曾开口向人借过钱?
姑姑张长英,是父亲的妹妹,比父亲小五岁,在郊区的红星乡下任教,姑父在乡镇企业当会计,小日子过得比我们稍微宽裕些。
每年过年,姑姑家都会给我包个大红包,里面有二十或三十块钱,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。
可现在要去借钱,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
去姑姑家要坐两趟公交车,再走半小时的土路。
那天早上,我揣着一块钱的车费,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裤,戴着父亲的旧帽子,踏上了去姑姑家的路。

天空阴沉沉的,像压着一块沉重的铅板,北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杨树,发出"咯吱咯吱"的哀鸣。
公交车上挤满了人,车窗上的哈气结成了冰花,我用袖子擦了擦,看到窗外的世界像蒙了一层毛玻璃。
两个小时后,我站在姑姑家门口,鼻尖冻得通红,手指僵硬得几乎握不成拳。
"谁呀?"门内传来姑姑的声音。
"姑姑,是我,小满。"我的声音被冻得有些发抖。
门开了,姑姑站在门口,一身灰色的家居服,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髻,看到我时眼睛一亮:"小满来了?快进来,屋里暖和。"

姑姑家的房子是乡镇分的福利房,两间正屋一间厨房,简朴但干净,炉子烧得正旺,屋里暖烘烘的。
"怎么想起来看姑姑了?吃饭没有?"姑姑一边说一边往炉子上添煤。
我搓着手,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
"姑姑,我......"我支支吾吾地开口,又停下来,不知道怎么说。
姑姑转过身来,目光柔和地看着我:"学校要交学费了吧?"
我愣住了,惊讶于姑姑的敏锐,随即点点头,眼眶有些发热。
"你爸妈身体都好吧?"姑姑又问。
我想起父亲临行前的嘱咐,咬了咬嘴唇:"挺好的,就是厂里这两个月效益不好,发工资晚了点。"
姑姑看了我一会儿,仿佛看透了什么,轻轻叹了口气:"等着,姑姑去拿钱。"
她进了里屋,我听到抽屉开关的声音,还有轻微的数钱声。
这时,屋角的收音机里传来《渴望》的片尾曲,那是当时最火的电视剧,刘慧芳的故事让多少人唏嘘不已。
姑姑出来时,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旧棉袄和一个白信封。
"天冷,路上穿着。"姑姑把棉袄和信封一起递给我,眼里有说不清的神色,"这是五百块,够吗?"
我接过信封,手微微颤抖。
五百块,那可是姑姑和姑父小半年的工资啊,我知道去年姑姑才添置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,花了将近两千元,家里肯定也不宽裕。
"够了姑姑,太感谢您了。"我急忙点头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"钱放好,路上小心点,这两年路上不太平,听说前段时间还有学生被抢了。"姑姑叮嘱道,眼神里满是关切。
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,穿上姑姑给的棉袄,那是一件略显陈旧但很厚实的棉袄,穿在身上顿时暖和了许多。
临走时,姑姑还塞给我两个鸡蛋饼:"路上饿了吃。"
回去的路上,北风更猛了,仿佛要把人吹进洁白的雪地里。
我缩在姑姑的棉袄里,心里却是暖融融的,那五百块钱像一团火,烧得我整个人都热乎乎的。
到家时已经是傍晚,昏黄的街灯下,我看到母亲站在楼下张望,那单薄的身影在风中摇晃,像一棵即将凋零的秋草。

"妈!"我快步走过去,把鸡蛋饼递给她,"姑姑让我带给您的。"
母亲接过饼,眼睛却盯着我身上的棉袄:"你姑姑给钱了?"
我点点头,从内衣口袋掏出信封,递给母亲:"五百块。"
母亲接过信封,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,又看了看我身上的棉袄,什么也没说,转身往楼上走去。
回到家,父亲已经出院了,坐在炉子边喝着稀粥,眼睛上还贴着纱布。
看到我回来,他微微点了点头,算是打招呼。
"小满回来了,先喝点稀粥暖和暖和。"母亲忙着给我盛粥,语气里透着疲惫和释然。
我脱下姑姑的棉袄,挂在门后的钩子上:"姑姑给了五百块,还有这件棉袄,说外面冷,让我穿。"
父亲听了,放下碗,长长地叹了口气:"你姑姑家也不宽裕啊。"
那天晚上,我睡得特别香,因为交学费的事终于解决了,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第二天清晨,我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。
推开门,看到母亲坐在桌边,面前摊着那件旧棉袄和一沓钱,她的肩膀微微抽动,泪水无声地流下脸颊。
"妈,怎么了?"我揉着眼睛问道。
母亲抬起头,眼睛红肿,声音哽咽:"棉袄夹层里缝着八百块钱。"
我愣住了,一时没反应过来:"什么?"
"你姑姑在棉袄的夹层里缝了八百块钱。"母亲又重复了一遍,声音颤抖。
我走过去,看到桌上确实放着一沓钱,崭新的一百元人民幣,足足八张。
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姑姑递给我棉袄时意味深长的眼神,还有她的叮嘱——"路上小心点,这两年路上不太平"。
霎时间,我明白了一切。
姑姑怕我路上遇到危险,特意把大部分钱缝在了棉袄里,表面上只给了五百,实际上却是一千三百块。
那一刻,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,酸涩又温暖。
"姑姑给了你多少?"母亲问,声音低沉。
"五百。"我低声回答,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母亲没说什么,只是默默地把钱收起来,小心翼翼地整理好。
我看着她略显粗糙的手指,想起这双手给我缝过多少衣服,补过多少袜子,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

"妈,对不起,我应该仔细检查棉袄的。"我低着头说。
母亲摇摇头:"不怪你,你姑姑也是害怕,才这么做的。"
她顿了顿,又说:"你姑姑一直很疼你,说你像她小时候一样爱读书。"
我点点头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"你姑姑年轻时也是个苦命人,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院,因为家里困难没去成,只能回乡下当民办教师。"母亲说着,眼神望向远方,似乎在回忆什么。
我第一次听说这些事,心里更加愧疚。
那天下午,我和母亲一起去菜市场,买了两斤猪肉和一些蔬菜,准备改善一下伙食,为父亲补身体。
市场上人声鼎沸,卖菜的吆喝声、讨价还价的争执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最普通却最真實的生活图景。
"肉涨价了,九块八一斤哩!"母亲看着肉价,皱了皱眉。
那时的物价开始飞涨,工资却跟不上,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越发艰难。
回家路上,我们路过一家国营副食店,橱窗里摆着各种罐头和饼干,门口挂着"购物满五十元送搪瓷杯一个"的招牌。
"妈,我们买点东西寄给姑姑吧?"我提议道。
母亲看了我一眼,点点头:"行,买点他们那边不容易买到的。"
我们买了两罐上海产的午餐肉罐头,一盒天津产的奶油饼干,还有一袋新出的"太阳花"巧克力,一共花了三十多块钱。
回家后,母亲找出一个干净的纸箱,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放好,又在上面垫了几张报纸,最后放进去八百块钱和一封亲笔信。
"明天你去邮局寄出去。"母亲说,声音里有一种释然。
晚上,父亲看到我们准备寄给姑姑的东西,久久地沉默着,最后只说了一句:"你姑姑是个好人。"
第二天,我按照母亲的嘱咐去邮局寄包裹,填写地址时,我的手有些颤抖,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姑姑的善良和信任。
从邮局回来的路上,天空飘起了雪花,轻盈的雪花落在脸上,冰凉却又舒服,像是上天在洗刷我的羞愧。
那个冬天,我穿着姑姑的旧棉袄,度过了高中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。

棉袄虽旧,却像母爱一样温暖,每当北风呼啸,我仿佛能感受到姑姑的关爱围绕着我。
两周后,姑姑来电话了,她说收到了包裹,也知道了我父亲住院的事,声音里有些责备:"有困难为什么不说实话?"
母亲接过电话,两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,最后都沉默了,电话那头传来姑姑低低的抽泣声。
那一刻,我才真正理解了亲情的分量,它不在言语中,而在那些无声的付出和默契里。
学费的事情解决了,我回到学校,更加勤奋地学习,仿佛这样才能对得起家人的付出和期望。
一九九一年夏天,我参加了高考,成绩公布那天,我拿着录取通知书,站在家门口迟迟不敢进去。
父亲看到我回来,放下手中的《工人日报》,摘下老花镜,问道:"怎么样?"
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他,声音因激动而颤抖:"爸,我考上了,省重点大学。"
父亲的手明显抖了一下,眼睛迅速变得湿润,他转过头去,假装看窗外,但我看到他的喉结滚动了几下。
母亲从厨房跑出来,看了看通知书,突然"哇"的一声哭了出来,那一刻,她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,又仿佛年轻了二十岁。
我们三个人站在逼仄的小屋里,谁也没说话,但心与心之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纽带,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。
第二天,父亲特意去集市上买了一只老母鸡,说要炖汤补补我的脑子。
那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下厨,他笨拙地杀鸡,笨拙地摘菜,笨拙地生火,但眼睛里却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彩。
母亲悄悄告诉我,父亲钢厂的同事们都知道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,都向他道贺,说他张长河有出息,养了个好儿子。
父亲在厂里抬起了头,走路的步子也比以前有力了。
我们给姑姑家打了电话,告诉她这个好消息,电话那头,姑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,只是一个劲地说:"好,好,太好了!"
那个夏天,我穿着母亲新做的白衬衫,走在小城的街道上,年轻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。
大学四年过得飞快,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,有了稳定的收入。

第一次发工资,我就回了趟老家,给父母买了新衣服,又去了姑姑家,把当年借的钱如数奉还,还带了一台新款收录机和一些营养品。
姑姑接过钱,却摆摆手笑道:"这么见外做什么?那都是亲情的本分,何必记这些。"
我坚持要她收下,姑姑看着我的倔强,笑着摇摇头,最终还是收下了。
pc28预测"钱我收下,但不是还债,是你的孝心。"姑姑说,眼睛里满是欣慰。
那天,我们坐在姑姑家的槐树下喝茶,聊起当年的往事,姑姑才告诉我,那件棉袄里的钱,是她和姑父攒了很久的,原本是打算换个新沙发的。
"那段时间,县里确实不太平,有几个外地来的流氓,专门抢学生的钱,我怕你遇到危险,就想了这个办法。"姑姑说,语气轻描淡写,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我看着姑姑略显苍老的脸,想起那件旧棉袄,想起母亲洗衣时的啜泣,想起姑姑递衣时的眼神,一时间百感交集。
多年后,我也为人父,每当看到孩子穿上新衣,我总会想起那件旧棉袄。
那不仅是一件御寒的衣物,更是一段关于亲情与尊严的无声诉说。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亲情是最温暖的棉袄,而尊严,则是棉袄里最珍贵的内芯。
如今,每当冬天来临,我都会想起那个年代,想起那件旧棉袄,想起那个雪花纷飞的日子,想起母亲和姑姑眼中的泪水。
那些记忆,像棉袄里的絮花一样,温暖着我的一生。